6月10日下午2时,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教授受邀于威廉williamhill体育名家名师学术论坛,在腾讯会议平台上为三百名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线上讲座。本场讲座由威廉williamhill体育中文系王攸欣教授主持,主题为“颠倒的书写与‘大哥’的困境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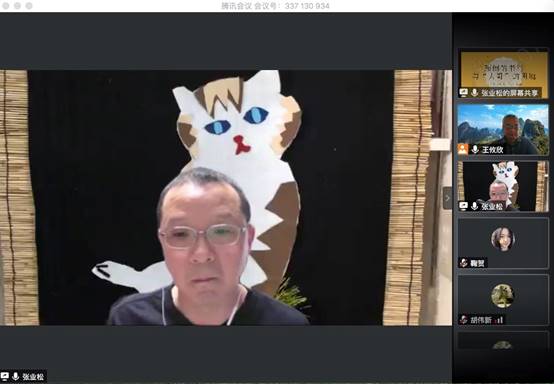
张老师首先指出,“大哥”作为问题始于《狂人日记》。在这部作品中,“大哥”作为“狂人”的对立面而存在,“狂人”形象的立足点和价值,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这种对位关系之上的。“大哥”在作品中的表现并非顽固守旧、不近人情,然而他却永远作为“旧”的一面的典型人物而存在了。这一艺术效果正来自于《狂人日记》首开其端的一种新文学的意义装置的作用:通过“颠倒的书写”制造内部之敌,以服务于新文学的意识形态目的。但是,由此体现的“编撰现代性”,也带来了使鲁迅深陷其中的“现代性困境”:“怎样做大哥”的问题从此成为这位现实中的“大哥”需要不断处理的议题。

接着,通过对《狂人日记》《我的兄弟》《风筝》《弟兄》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等作品的解读与比较,张老师详细阐述了鲁迅对兄弟关系议题的处理。
他认为,《狂人日记》中担负起“长兄为父”职责的大哥,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形象。尽管在外人面前,大哥表现出完全的权威和主宰地位,但是,从他对弟弟的教育、日常管理中,不难看出大家长温和负责的一面。
《我的兄弟》和《风筝》中的大哥更多地表现出了建立于幼者本位意识之上的反省与忏悔。对读这两篇作品,可以发现鲁迅对父亲之死采取了不同的叙述。《风筝》放大了父亲的死,这一改写背后隐含着兄弟失和的隐痛,作为兄长的“我”被迫承担起责任,这一改变塑造了“我”的人生观和性格,也改变了小兄弟的兴趣爱好,所以“我”对小兄弟的改变是有责任的。到这里,作为个人所需要的承担和面对的一切才凸显出来,这也是“大哥”复苏的契机。
分析《弟兄》一文时,张老师认为我们应该看到大哥在维持兄弟关系中的压力与痛苦。从兄弟怡怡到鹡鸰在原,《弟兄》所要表达的含义是:做大哥的前提和做好兄弟的根本性立足点都是做好自己。
张老师强调,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指向的不仅是怎样做父亲,还包括了怎样做大哥和怎样做觉醒的人这两个议题。在这篇文章中,鲁迅倡导的是从生物进化论走向人的内在进化论。“大哥”议题通过不断的思考与延伸,指向了鲁迅的“成人之学”,即用启蒙主义的理性去思考,强迫自己去改变,内蕴一种内在向上的动机,实现一种现代人格的成长。
在讲座最后的互动环节中,与会师生踊跃提问、积极留言,提出许多见解独到而又引人深思的问题,与张业松教授进行了精彩的交流。讲座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圆满落幕。
邹诗雨(威廉williamhill体育文新院中文系16级本科生)
2020-06-12 15:56
编辑:鞠鹤
审核人:审核人参数配置未打开
分享





 分享:
分享:



